爱因斯坦在上海接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式通知
1922年爱因斯坦受到邀请去日本访问讲学,往返路途经过上海,去程11月13日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得到瑞典驻上海领事馆正式通知: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决定推迟了一年。当时他应该住在。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神户庆应义塾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讲学途中,顺道前来上海。他偕夫人艾尔莎从德国柏林出发,先到法国马赛港,乘日本邮船“北野丸”出发,前往东方。同船而行的有日本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夫妇、日本贵族院议员德川义亲候爵夫妇、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鸠山秀夫博士等人。他们穿过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在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都作了短暂的停留。
在印度时,他和诗哲泰戈尔在后者于博尔普尔创建的桑地尼克丹学校(意为“和平之居”,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相处了几天。11月10日,在他临近上海的时候,船上的无线电广播中传来了他荣获1921年诺贝尔学奖的消息。
“北野丸”原定11月12日抵沪,但延误至13日上午11时才抵达汇山码头(一度改称“上港三区”,现名“汇山装卸区”)。前来迎接的有德国驻沪总领事和旅沪德侨菲斯德博士夫妇等。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和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村田,陪同爱氏夫妇乘汽车浏览了上海的南京路等街道市容,并到“一品香”午餐 (“一品香”是当时有名的旅社,在今西藏中路、福州路以北,其餐厅以中式西菜著称,原址现为岷山旅社)。当爱因斯坦在南京路被认出的时候,狂热的青年学生们高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众人把他高抬起来,以能触摸到爱因斯坦的身体为荣。爱氏夫妇于3时入城内,在“小世界”聆听了昆腔(“小世界”是当时的游戏场,在今新北门内福佑路、城隍庙后,原址现为文化电影院),游览了城隍庙(豫园),到画家王一亭住宅出席了中国文化界的欢迎会 (1867-1938年,名震,别署白龙山人,工书画,擅绘佛像),作陪的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的经理曾谷冰和主编张季鸾、北大教授张乃燕等人,观赏了中国美术,并进晚餐,品尝了中国菜肴。爱氏对之的评价是用脂油太多,恐不易消化。席间,有一个年仅11岁、名叫应惠德的小女孩,能以德、法、英三国语言与爱氏夫妇交谈,使他们惊讶不已。饭后,日本学士会又宴请他们于日本俱乐部。此外,他们还在菲斯德博士家与旅沪德国人开了茶话会。而希尔施拉比 (rabbi w. hirsch,拉比是犹太教的教士)为首的犹太人代表团,则向爱氏夫妇转致了当地犹太社区的问候,并邀请他们在下月返回上海时出席社区的招待会,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11月14日,爱因斯坦夫妇由稻垣夫妇陪同,乘原船前往日本。在日本,爱氏的讲学大受日本人欢迎。爱氏在讲学之余,还饶有兴趣地对日本的风俗、民情、建筑、音乐进行了考察。12月27日下午,爱氏夫妇由门司乘“榛名丸”启程返回欧洲。12月31日,再度抵沪,逗留至1923年1月2日离去。
1923年元旦,爱因斯坦在工部局礼堂作了有关相对论的讲演。同日下午,他还出席了上海犹太宗教公会(shanghai jewish communa1 association)的招待会。晚间,又参加了犹太青年协会(youn men′s hebrew association)和探索社(quesg society)联合主办的相对论座谈会。
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的招待会由犹太人加登(s. gatton) 夫妇为东道主,在杜美路9号他们宏伟的住宅举行(该建筑后改为杜美大戏院,现名东湖电影院,杜美路现名东湖路)。上海犹太人社区的名流大都出席了招待会。会上,爱因斯坦应邀谈了创建伊始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的发言是用德语讲的。他的夫人则说得一口英语。因此,他们同与会者没有语言上的隔阂。
宗教公会主席大卫在欢迎词中,介绍了爱因斯坦。会上,希尔施拉比的夫人代表上海犹太妇女界,向爱因斯坦夫人赠送了精美的中国绣花披巾。
在晚间的相对论座谈会上,探索社的主席查特莱(h.chatley)博士认为,在那样的群众集会上无法详细讲解相对论的原理,因而提议由与会者直接向爱因斯坦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请他解疑释惑。到会者纷纷提出了问题。有人问,爱氏是否认为,迈克耳孙-莫雷(michelson-morley) 实验已足够精确,可据以假定真空光速为一恒量。爱氏答复时,提到了菲佐(fizeau)的基本实验、光行差和麦克斯韦-洛伦兹(maxwel1-lorentz)的电磁说,认为据此必然作出上述假定。查特莱本人问,不久前远征队赴澳洲观测日食的结果如何? 爱氏答,结果尚未公布,可能需数月之久。他说,要在照相片上测出星体的百分之一毫米级的细微偏差,并由此计算出偏差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工部局电气处的一位安东尼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他问,能否用木卫掩星现象(小行星在运行中遮掩了背后的恒星,其原理与日食相似,是罕见的天文现象)证明相对论的正确。爱氏答,不仅结果可由此推论,而且他确实知道,这一问题正在计算,可能得出结果。对于以上的和其他的提问,爱氏都能立刻抓住其要点,微笑着走向黑板用图例说明,或用口头阐释。他的回答简短而直截了当,要言不烦,一如读过他著作的读者所熟悉的那种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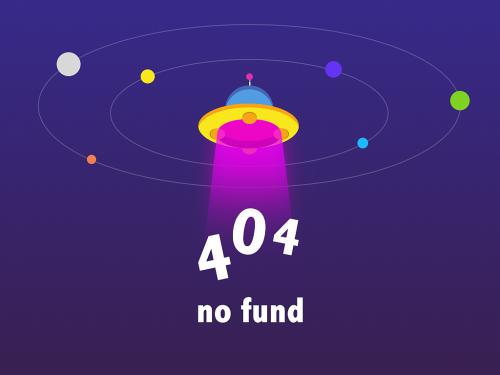
对于爱因斯坦的两度访沪,上海当时的中、外文报纸《申报》、《时报》、《大陆报》(china press)、《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以色列使者报》都作了报道。《时报》连续多日发了消息。1922年11月15日的新闻中,对爱氏的写照是: “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村庄传道教师(士)。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髭黑,发灰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生动地绘出了爱氏给上海人的最初印象。该报11月20日的图画周刊,并登有爱氏到沪时偕夫人在轮船上的合影。《申报》除发消息外,还在岁末、年初的两期星期增刊中刊登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大教授丁巽甫讲演、刘元斗笔记的《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一篇是法国夏尔·诺德曼(char1es nordman 物理学家,为在法国传播爱氏的思想做了许多工作)著、lk译的、介绍相对论的《人类思想界之大革命》。《大陆报》除详细报道了爱因斯坦出席前述招待会和座谈会的情况外,在1923年1月7日还刊登了《科学家拍摄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的长文。该文与1922年《科学》第7卷第11期的“科学新闻”,都记叙了世界各地观测1922年9月21日之日全食,以证实或否定相对论的经过。在这以前,英国皇家天文台已根据1919年5月在非洲和巴西观测日全食之结果,证明相对论的正确,使爱因斯坦名闻全球。但科学界有人对此观象结果尚有怀疑。故各地天文学家乘1922年9月21日再次日全食的机会,纷纷选择适当地点,如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爪哇西南的圣诞岛,以及澳洲的瓦拉尔(wallal)、贡迪温迪(goodiwindi)、科尔迪洛砂丘(cordillo downs)等处、再度进行观测,期望在相对论的问题上得出一无可怀疑的证实或否认。《科学》的新闻,略述了南印度的科迪亚卡那尔(kodiakanal)天文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美国加州的利克(lick)天文台、西澳洲的珀斯(perth)天文台,以及荷兰、德国联合远征队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远征队,分赴各地观测日食的概况。《大陆报》的文章则是一篇出自利克天文台台长坎贝尔(w. b. campbll)教授笔下的专稿。,他详细地叙述了率领克罗克远征队(crocker expedition)前往瓦拉尔,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观测日全食的艰苦经历和丰硕成果。瓦拉尔的日食历时最长,为5分19秒,而且天气晴朗无云,使观象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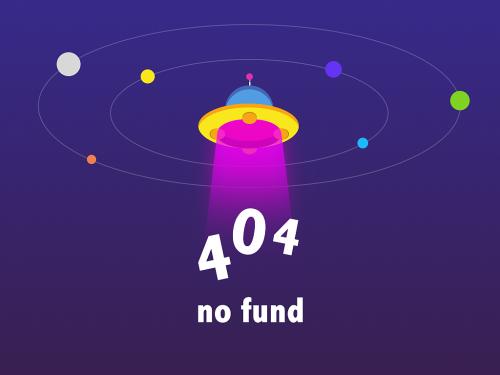
杂志方面,商务印书馆的读者面宽、影响力大的《东方杂志》,在1922年12月25日,亦即爱因斯坦再度访沪的一星期前,以第19卷第24号的一期为“爱因斯坦号”,收有论文10篇以及爱氏的小传和著作目录,并刊印了爱氏夫妇的合影照片。李润章的《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援用了法国的郎之万(paul langevin,文中译作“郎曰曼”)的讲演,心南的《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取材于上述石原纯的讲演。周昌寿(即周太玄)的《相对性原理概观》,则是一篇独立的创作,扼要地分节介绍了相对论的起源,狭义相对论(当时译作“特殊相对性原理”),广义相对论(当时译作“普遍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的宇宙观、能媒观以及魏尔(claus hugo hermann weyl,文中译作“外尔”)相对论的新发展。周昌寿的文章,除了上述介绍爱氏科学理论的章节外,又提出,“现在适值爱因斯坦将来华讲演,我们一面预备欢迎他,一面就不可再蹈这种盲从的恶习。务必要踏踏实实的将他真正的价值研究一下,要不然,恐怕不特我们这一番景仰思慕的感怀无由表示,就是爱因斯坦先生对于这样毫无了解的欢迎,也决不会表示满意呢”。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科学家的心声和学习爱因斯坦应持的正确态度。
商务印书馆还在《申报》1923年元旦一期发出广告,说明该馆“备有几本相对性原理的书籍,介绍博士的为人和他的学说”。这些书籍,有的已经出版,有的正在印刷。其中有一本是著作,即周昌寿的《相对律之概念及其由来》,其余均为翻译,如: 周昌寿、余祥森合译的《康德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周昌寿、郑贞文合译的《爱因斯坦和相对性原理》,郑贞文编译的《最近物理学概观》,闻斋译的《相对性与宇宙》,费详译的《通俗相对论大意》、张哲甫译的《相对论的根本思想》。
还有几则报道,《时报》1922年11月15日的报道中,曾有“且(日)下北京与金陵二大学(金陵大学在南京,原址现为南京大学),已邀博士演讲”,以及“如有暇,或参观圣约翰 (指圣约翰大学,原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与大烟厂”之说,但后来未再有这方面的报道,看来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些计划似都未实现。
苏联里沃夫(v.lvov)所著《爱因斯坦传》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9-180页提到,“11月15日,中国大学生在上海为了此事(指爱氏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对他作了热烈的欢迎,用手臂抬着他在南京路上走过”。这应该是11月13号的事情。
诺贝尔奖为何迟到了一年?
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为何姗姗来迟,直到1922年11月,才宣布授予爱因斯坦呢?而与爱氏同时获此殊荣的波尔(niels bohr,获物理学奖)和贝纳文特(jacint benavente,获文学奖),得到的却是1922年度的诺贝尔奖金。这是什么缘故呢?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爱因斯坦就表现了他一贯捍卫自由、和平、社会进步的鲜明立场,支持《告欧洲人书》,反对为德皇歌功颂德和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宣言》。德国投降后,战败的军国主义者迁怒于人,把犹太人当作泄愤的对象。爱因斯坦既有犹太血统,又持鲜明的正义立场,再加相对论的大获成功引起敌对者的妒意,自然成为众矢之的。20年代初期,在德国,随着纳粹的得势,酝酿了一个反相对论运动(这怎么跟我们文革初期有点向象?)。1920年8月,在柏林音乐厅,敌对者精心炮制了一次反相对论大会,爱因斯坦也应邀出席。会上,敌对者以纯洁科学工作为幌子,乘学术辩论之机,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政治咒骂和人身攻击。爱氏坦然而耐心地听取了意见,随后在《柏林日报》上点名批评了反对相对论的莱纳德(philipp lenard)。莱纳德曾获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爱因斯坦认为他在实验物理学领域虽有成就,但在理论物理学方面不行,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十分肤浅,没有必要详细回答。爱因斯坦的反驳,使得莱纳德和另一个在1919年刚获诺贝尔奖金的德国实验物理学家斯塔克(johannes stark)恼羞成怒。两个人同爱因斯坦的私交本来都还不错,但随着纳粹的日益得势和反犹浪潮的甚嚣尘上,他们反对爱因斯坦不遗余力。他们得知瑞典皇家科学院考虑,由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上的成就而授予他诺贝尔奖时,就发出抗议,无视不久前英国皇家天文台已根据观测日全食的结果,得出相对论正确的结论,硬说相对论荒谬透顶。他们并威胁说,要是爱因斯坦获奖,他们就将退还自己的诺贝尔奖。这使瑞典科学院左右为难。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当时有一个传统,要把奖授予具体的发明,而且是没有争议的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明。瑞典科学院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因此迟迟未作决定,在隔了一年后,才巧妙地采取了折衷的方法,在宣布授予爱因斯坦奖时,说明授奖原因是“由于他的光电效应定律和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迥避了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尽管如此,莱纳德还是向瑞典科学院递交了抗议信。这是一场硬把政治斗争屏入科学研究的历史闹剧。
爱因斯坦与丹麦的玻尔于1922年11月同时被宣布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并非合得同一年度的奖金,而是分别获得前后两个年度的奖金(1921和1922)。二人就此事的来往短信,言简意赅地表现了两位大科学家相互敬重、倾慕之情。玻尔1922年11月11日的信中说“关于授予诺贝尔奖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1923年1月11日的回信波尔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你的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象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至于爱因斯坦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被他全部转赠前妻米列娃·玛里茨,作为她本人和两个儿子的生活费。
爱因斯坦两次访问上海,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他以犹太人在排犹的德国受歧视、排挤、迫害的经历,身同己受地目睹了上海人民受到殖民者的欺凌压迫,对此深表同情。他的女婿以安东·赖洋(anton reiser)为笔名撰写的《爱因斯坦传》,根据他当时的旅行日记,对此作了报道。书中说,“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 (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者)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对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作出了这样深刻的观察。十多年后,1936年11月,鼓吹抗日救国的沈钧儒、邹韬奋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事件”发生。消息传到美国后,爱因斯坦联合美国文化界15位名人,通电蒋介石、孔祥熙等,声援“七君子”,要求释放。《救国日报》1937年2月5日刊登了电文,电文说,“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再度表示了爱因斯坦主持正义和关切中国人民的感情。
主要资料来源:



